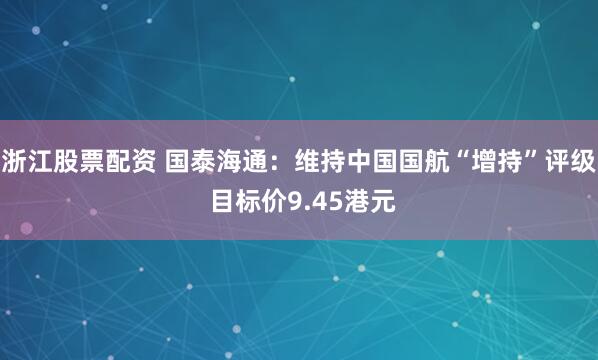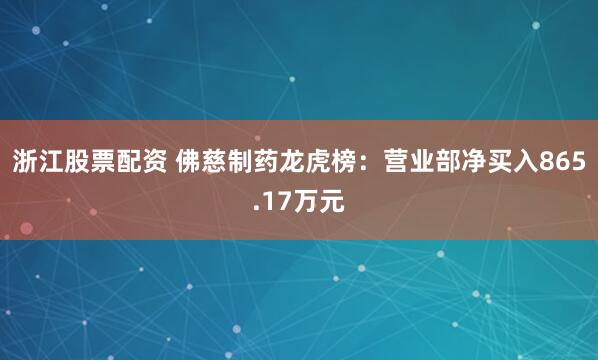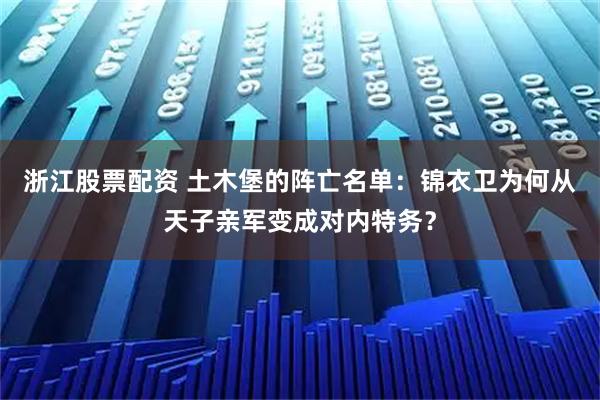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浙江股票配资
字数:3254,阅读时间:约9分钟
编者按:提到,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务组织”四个大字。但事实上,明代锦衣卫虽然有着很浓重的司法和监察职能,但除此以外,至少在明朝中前期,锦衣卫作为明代亲卫军的一员,其军事职能也并不薄弱。
举一个人数上的例子,永乐时期明朝共在辽东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而作为亲军卫之一的锦衣卫,其下辖的千户所就多达19个。其中更是有专职骑兵千户所4个,如此庞大的兵力配置,只用于监视和谍报工作似乎有些过于夸张。
事实上,明代军队的设立同样遵从居重驭轻的原则,明代京卫总兵力本就远超过地方,战事发生时,往往会以京军作为主要参战力量。而隶属于亲军卫的锦衣卫自然也不能例外。
锦衣卫前身为都督府下正七品拱卫司,后升为正三品的拱卫指挥使司。不久后,又改名为都尉司、亲军都督府:“洪武三年,改亲军都督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而设仪鸾司隶焉。”
洪武十五年(1382),罢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改设从三品锦衣卫统辖事权,为从三品,两年后,改从三品为正三品。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朝锦衣卫虽有侦缉监察之权。但其军事职能却并未因此而消失。
举个例子,洪武十四年云南之战是明开国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南征。战役结束后,明廷本准备依遵循惯例由当地军户填充新设卫所,然而,此时云南历经兵祸,“图籍不存, 兵数无从稽考”。
无奈之下,只得从外卫、京卫抽调军士至当地屯驻,镇压反叛、控制局势。洪武二十一年,又再次于当地增设景东、蒙化二卫,并“以锦衣卫指挥佥事胡常守景东,府军前卫指挥佥事李聚守蒙化”。
对胡常的任命并非个别锦衣卫将官的人事调动,根据《游牧文明因子与明朝卫所体系中的亲军卫——以锦衣卫为中心的考察》的作者张金奎对《云南后卫选簿》《临安卫选簿》《安南卫选簿》等资料爬梳,胡常调至景东卫的同时,大量锦衣卫官兵也在向景东卫等地抽调,如福建清流县人魏荣、 浙江仁和县叶胜保、广东怀集县黎亚章等人,都是以锦衣力士(锦衣卫基层士兵,无品秩)身份调至景东卫。
由此来看,在洪武时代的锦衣卫和其他京卫一样,仍需要外出作战乃至执行屯戍任务。

洪武末年锦衣卫的侦缉监察之权遭到裁撤,司法权转移给三法司:“
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稍稍夷它军矣。
”但随着靖难之役的结束,以“清君侧”名义登上皇位的明成祖朱棣再次启用锦衣卫,设锦衣卫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审讯犯人, 与三法司共同执掌司法,权势大增。
与此同时,靖难之役中以军功提拔的武官们也有不少被调入锦衣卫任职,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因为锦衣卫“侍卫亲军”的属性太过强烈,朱棣主要从燕王府仪卫司、燕山山左中右三户卫等元从部队中擢拔将官至锦衣卫,以北平诸卫为例,《南京锦衣卫选簿》中仅一名叫做屈士通蓟州卫左所试百户因战功升锦衣卫中左所世袭正千户。
靖难之役后擢拔的大批武官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增设典狱,锦衣卫本身就是天子的侍卫亲军,因此,在永乐皇帝五次亲征蒙古的战事中,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官们也会随驾出征,护卫皇帝,亲履战场。

除了北平诸卫的武官外,在永乐时代,蒙古、女真降人同样是锦衣卫重要来源之一,明成祖曾在辽东设立将近180个卫及20个所,而通过从奴儿干、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招抚,收容了大量蒙古、女真降人。这些降人中大多有部署跟随,其首领则以于锦衣卫食粮带俸的身份,录入锦衣卫选簿中。

事实上,招抚边地各族降人是明初就已经开始实行的政策,“
凡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
(《明太祖实录》)。而由于归附者中以元朝部队中归降明朝的达达等族人数最众,当时人们也将这些武官称为“达官”。
这些达官往往精通骑射技艺,战斗力惊人。一方面为发挥其军事价值,另一方面为方便管理和监督,达官多被编入卫所之中,安插到全国各地。例如,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其部下多 被 “
授以指挥、千、百户,食禄而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
和一般意义上的将领不同,达官在有自己专门的贴黄册,编号用 “达”字 (其他武官用 “武”字),而锦衣卫中的达官更是只营操而不理军政,也不用参加军政考选。可以想见,这种方式挑出来的锦衣卫自然不会是用来侦刺不法的密谍,而是最懂得“以德(武德)服人”或者“以理(物理)服人”的武人。

即使到了正统年间,锦衣卫武官参与出征的记载也并不罕见,如正统七年(1437),锦衣卫武官武忠以先锋官身份在白海子一带大败蒙古骑兵,而在五年前,他也参加了铁岭卫附近的明蒙冲突。
土木之变时,大批锦衣卫军官随驾扈从,战死于土木堡,比如锦衣卫百户路俊,在明军大败之际溃围而出后,并未逃走而是转身反复冲杀瓦剌军阵,力战而死。;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的胡濙(坊间传闻中他奉朱棣命令暗访建文帝行踪),其子胡谸为锦衣卫千户,随英宗北征,也阵亡于土木堡之役。
事实上,除了以上两人外,《锦衣卫选簿》还记载了大量在土木之役后“征进未回”的锦衣卫千户、百户等级别的将官,可见锦衣卫系统也在此战中损失惨重。

那么,锦衣卫刀刃向内的传统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或许与明孝宗有关。土木之变后,为解决京畿防卫兵力的问题,景泰帝同意了于谦“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的计划,自三大营等部队中拣选可用之兵,作为团营精锐。
而锦衣卫中自然也在拣选之列,然而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兵部本依照前例奏 “以锦衣卫及腾骧等四卫军旗勇士校尉六万八千余人选补团营之缺”,但这一请奏遭到御马监太监宁瑾等人的反对。
到了最后,明孝宗并谕令“今后各衙门查理戎务,不许以五卫混同开奏”。这意味着自此之后,锦衣卫不再参加团营选拔,无需出京作战。

很难说锦衣卫军事职能的消失就是一种退化,事实上,明代锦衣卫除了人们印象中特务机构这一种属性外,其职能的边界相当混乱。其职责的增设更是叠床架屋,层出不穷。
晚明时,锦衣卫堂上官中甚至有“提督街道房官旗办事锦衣卫管卫事某官”这类官职存在,按照万历《大明会典》中的记载,“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本卫指挥一员,奉旨专管,领属官二员,旗校五十名。所谓的街道房,和明初锦衣卫中就存在的东司房、西司房不同,属于后来增设。
这属实是锦衣卫和街道办大妈的梦幻联动了,街道房的职责也相当明确:“化二年,令京城街道沟渠,锦衣卫官校并五城兵马时常巡视。如有怠慢,许巡街御史参奏拿问。若御史不言,一体治罪。”
《明实录》也有载:“街渠污秽、壅塞”,中城兵马司指挥、巡城御史和锦衣卫官校也要被逮捕入狱,“令法司议罪以闻”。
这倒不是哪位皇帝脑洞大开,事实上,当时京城中权贵要人随意侵占、开挖街道的情况屡见不鲜,“京城内外势豪军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沟渠.......”(《明武宗实录》)
而原先负责街道管理的五城兵马司和巡城御史官衔、权限都太低,人微言轻难以处理,而工部又以只管理工程事宜为由推诿塞责,不得已之下,拥有缉捕权利的锦衣卫就这样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与之类似,为了打击私自宰杀耕牛的行为,明廷还赋予锦衣卫抓捕“违禁屠牛人”的权利。但耕牛究竟是病死、老死、意外受伤死亡还是确属于私宰本身就很难甄别,而一旦大规模缉捕很容易引起一系列问题,如成化年间,因为“杀一牛罪至罚十”,竟然导致一些军队采购牛皮、牛骨、牛筋、牛角等军需都困难非常,朝廷不得不“喻东厂官校莫加刺访”,这一禁令自此才变得名存实亡。
值得一提的是,和大多数朝代的禁军一样,中后期的锦衣卫中大量充斥皇亲、宦官弟侄出身的锦衣主事军官。甚至于,一些受到皇帝赏识的画师、工匠,也会被安置进锦衣卫当中,这种人员成分上的转变,或许也是锦衣卫军事职能日益减少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范博忱《明代锦衣卫军事职能研究》
2、张金奎《明中叶锦衣卫职能的延展与本体变革》
3、张金奎《游牧文明因子与明朝卫所体系中的亲军卫——以锦衣卫为中心的考察》
4、梁志胜《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红太阳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